你捧读那本会在黑暗中裂出细纹的书,任由那浓墨重彩沁入肌肤纹路,钻入血液骨髓,正好让你感受其中与干涩喑哑并存的残忍与暴烈。等你回过神来,离开那些幽深与离奇,再看世道,就会发现“在这里,或那里,都没有多大的分别”。
只有她的故事,在心里如一堵旧影斑驳的墙,由于光的照射,正在渐渐剥落。
在那个琼瑶与金庸融进几乎每一个香港人血液的年代里,韩丽珠由于读到了三岛由纪夫的作品而惊叹“文学也可以这样写”;而我偶得韩丽珠的小说,产生了一种与她相似的,从很久之前流传至今,不知出处的感慨。
我知道,韩丽珠读三岛所谓的“这样”与如今我读韩丽珠所谓的“这样”一定是大相径庭的。比如在关于“美”的字眼上,三岛但凡写到它,都倾向于一种歇斯底里的,与毁灭同在的感受。不论是从《金阁寺》中说的“美的东西,对我来说,是怨敌。”还是遗作《天人五衰》中“知而犹美这样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。”都不难看出在三岛的文学如精致丝绸覆盖的表层背后,那惨烈且无法抗拒的时代,或说是世界。
这恰好映证了三岛的那句话:“这个世界早已炼就金刚不坏之身,任何人都奈何不得。”不论它有着怎样让人厌恶的面孔。
关于抗拒与被抗拒,在韩丽珠的小说中都不显得如此决绝。相反,她的很多故事都是血脉相连的存在,你只要停顿在某个孤独的阴影背后,细细观察它不断重叠的表层,就可以顺着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脉络摸索出文字的形体来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她早期文字《坏脑袋》(短篇小说集《风筝家族》)中被人抗拒的白;《林木椅子》(短篇小说集《风筝家族》)中抗拒为人宁愿当各种椅子的林木;《灰花》中抗拒执法者的市民;《缝身》中抗拒连身的主角“我”与抗拒不参与缝身市民的社会;直至近来《飞翔》(香港文学》325期)中抗拒管辖者的卖气球的男人和众多贩卖者。这种种的对世俗的抵抗虽不一定都是有效的(不如说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),那如蚁族一般只有微力的人,仍旧在铺天盖地的阴霾下,顶着一张张轮廓模糊的脸,驱动僵硬的身躯,对这不可适应的世界做最后的抵抗,像艾略特所说“他们生活在人们被幻想所浸润的年代”。
说及幻觉,一直让我觉得是韩丽珠的另一个代名词。她自己亦曾在某篇后记中自问自答:“真实在什么地方。有时候我似乎能肯定它在哪里,但一不小心便会发现那不过是另一种幻觉而已。”读她的小说,最先蹿进脑袋中的词是“荒诞”,这种荒诞表现得非常明显,她从未想过要将其隐藏。她描述的世界中总有一种并不合理却又傲然挺立的事物,就算是那些被描摹得有智慧的人,都没有觉得很多事情之不合情理。人们像是被她文字里常年阴翳的天空所渲染了,这几乎贯穿了她所有文字,让那些在不自然环境中生长的人适应每一种不自然,并企图将其转化为最平凡的事情,世道变换,但那需要抗拒的东西却让人们像是“掉进那洞穴里”一样,始终存在着。
深陷其中的人,像是被蒙了眼,伸出手想要摸索以后的路,但处处碰壁,只好不断蜷缩,不断折叠,最终变成一个渺茫的、不易被发觉的点。也许有一天,这个点会不断扩大,起先只是长在墙上的,最后总会折射到别人的眼中、心里。但这个“有一天”实在难以推敲,也许是几年,或是几个世代,因为在韩式故事中从来都没有确定的时间或空间。
当下大多叙述者为了编造一个看起来完整或无懈可击的故事,总会为他们的故事冠上某年某月的标签。可是与此不同,韩丽珠从不提及具体的时间。不论是小说《睡》(短篇小说集《宁静的兽》)的开头如是说“他已经沉睡了十个月”,或是《梦游症旅行团》(《文学世纪》38期)中“那是夏天才开始的事情”,还是《缝身》中缝身法律的确定“必定早在很久之前 ,这样的安排便已经确定 ,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共同承担责任。”就算是家族史《灰花》的换代也只能找到一些浮光掠影:“另一天开始之前,她越过医院的栅栏,溜回自己的床上,躲进被窝里,耐心等待新的胚胎在自己的体内形成。”
我时常想象,那些原本应该存在于小说中的时间,不知道什么时候偏离了预定的轨道,掉落到了故事之外,一定是在不经意的时候被韩丽珠偷走了,她将之紧握在手中,每一次只分配一点,因为若是让一本书,一个人来承受这发黄的受潮的,不断在扩张蔓延的时间,那必然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。而韩丽珠的残忍不在这里,是在那些无法抗拒之中,抑或是,她忍受不了这种残忍,不然也不会有类似“衰老原来并不是生理状况,而是,一种埋在生命深处的疲惫,以及无法僭超时间表的消极愤怒”的感悟。
另一种,所谓的没有空间,是空间的桎梏。她笔下大多数故事,都发生在极其微小的范围内,甚至还在不断缩小,就像刚才所说的,她恨不得让它们无限折叠,变成一个不被人重视的点。比如《界面》(《自由时报》专栏)中在笼内蜷缩身子的妻子;《壁屋》(《香港文学》191期)中“我自小渴望住进壁屋里,但没有说出来,另一个我走到我身旁,对我说出相同的渴望”的主角。而《灰花》涉及流亡,本该写到大面积的迁徙与离散,写尽悲歌与泣血,但韩丽珠只字未提,反而在其后说及封闭的地窖与被执法者看守的大楼,将那原本应在大空间内发生的事情,似小孩堆积沙堡一样,不断将周围的流沙刨空,向某一个原点的高处建筑,也宛如那些不停建造的高楼,人们仰起头来看时,总有一种它终将穿破天空,直达碧落的错觉。
奇怪的是,这种不断被淡化朦胧的时空,却会让人很自然地想到当下的香港,输水管不断层叠到高处的香港,睡眠常常被限制的香港,人与人之间相互排斥的香港,即使缝身也只能越来越孤独的香港。香港这城市的坚硬与冷漠横在人的眼中,化不掉,也驱不走。《灰花》中死者被烧成灰烬,是为了保持城市的秩序,但那骨灰弥漫的阴霾,终要回到原来的地方,污染每一寸的可见度,你越想要忽视它,它却会越发靠近你。
就是在这些闭塞的,像是暗室一样的空间中,我仿佛看见了伏案的韩丽珠在奋笔疾书。我想象她在一间空无一人的房间里,点了盏明灭的灯,她在发呆,或书写,将构筑的世界推翻,重新幻想一个离奇故事。也许就像她自己所说的“当我已逐渐习惯那房子内的一切,那房子再也不是一幢悬在半空的房子。”当她书写时,目所能及的一切也将会被重新定义。她像是在密室中绽开的花,不必有人驻足,也可以孤芳自赏。
正因如此,置身于韩丽珠所勾勒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中,眼睛像藏了一只要挣脱出来的飞蛾,那故事浓烈的色彩几欲从字里行间渗透出来。你捧读那本会在黑暗中裂出细纹的书,任由那浓墨重彩沁入肌肤纹路,钻入血液骨髓,正好让你感受其中与干涩喑哑并存的残忍与暴烈。等你回过神来,离开那些幽深与离奇,再看世道,就会发现“在这里,或那里,都没有多大的分别”。
只有她的故事,在心里如一堵旧影斑驳的墙,由于光的照射,正在渐渐剥落。
作家简介
韩丽珠,1978年生于香港,被董启章称作“香港最优秀的年轻作家”。著有《灰花》、《风筝家族》、《宁静的兽》及《输水管森林》。曾获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、第20届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、2008《中国时报》开卷好书奖、2008《亚洲周刊》中文十大小说等。《宁静的兽》获第8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小说组推荐奖。《风筝家族》获台湾2008开卷好书十大好书中文创作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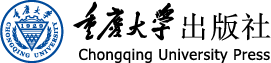

 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渝公网安备 50009802500702号

